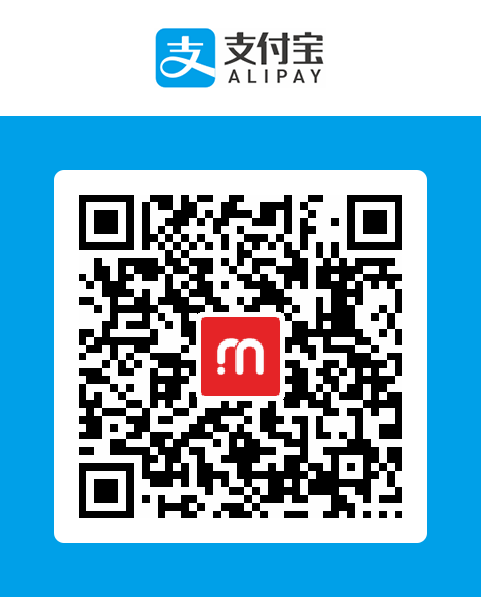(19)参见张慰:《艺术自由的文化与规范面向:中国宪法第47条体系解释的基础》,《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黄明涛:《宪法上的文化权及其限制:对文化家长主义的一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这部基本法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事实上成为两德统一之后的新宪法。该动议以211票对89票获得通过,最终落实为魏玛宪法第3条的规定:国旗颜色为黑、红、金三色。

但是,目的法学(Zweckjurisprudenz)明确反对这种倾向,并且指出,法律无法避免受到目的(Zweck)的支配,而目的并不能来自于规范体系的内部,这相当于再次强调了事实优先的原则。……我不需要进一步去反驳这样的论点。普罗伊斯提出的这一方案完全排斥象征着普鲁士的因素,可见,魏玛宪法中的Reich一词在其心目中并不存在与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任何关联。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三个故事之外同时添加更多与之平行的维度,例如,从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魏玛宪法第148条第3款关于开设国民常识与劳工课程的条款为中心,探讨德国国家基础教育体制的历史变迁。仅过了两个月,6月27日,右翼政党向帝国国会(Reichstag)进一步提出取消在商旗的上内角镶嵌黑、红、金三色国旗,这是无视宪法的举动,是对魏玛宪法所确立的共和制的又一次公然挑战。
国家力量在瞬间坠入虚空,还引发了另一种现象:极端的政治派别大量涌现出来,他们试图把德国变成激进政治理论的试验场,在一系列过激的社会运动中,那些残存的、对于国家可能有益的政治事实遭到了进一步的摧毁。这一叛乱行动具有强烈的复辟和反对共和的象征意义。[29]You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Chapter 11. [30]事实上,中国互联网法律法规也是按互联网分层结构进行规定。
正因为网络空间互相连接、共同操作的性质,针对位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互联信息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效果。当一国国民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为了消除这种威胁,一国也就具有侵入别国领土空间进行干涉的正当性。倘若不加区分地在每个层面都适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处理问题,反而无法实现应有的规制效果。[39]从战略学角度来看,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陆地、天空、海洋和太空之外的第五疆域(the fifth domain),[40]成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新战场。
例如,在苹果公司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一次纠纷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调查枪击案嫌犯信息,让地区法院发出命令,要求苹果开发后门软件,以便破解该嫌犯的iPhone5c的密码。历史上,秉承主权否定论思想的一些工程师和互联网人士,曾经试图采取网络空间自治的模式来解决 DNS 系统的治理问题。

2015年,美国政府还推动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签署,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2个国家都参与其中。首先,它会影响一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37] 由此,美国也将保护国家网络关键设施作为其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在极端情况下,二者甚至对于数据控制权产生争夺。
一国攻击另外一国的网络基础设施的行为将侵犯该国的主权。最后,在主权概念应用于具体法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理解和尊重互联网架构体系的分层特征,根据物理层、逻辑层和内容层各自不同的联结属性和国与国之间互相勾连的程度,进行相应的制度匹配。[17]由此,欧洲大陆迎来了近百年的相对和平,这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14]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新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争夺,尤其是数据争夺的日益激烈化,主权肯定论的说服力也越来越大。其次,实施主体是多元的。

较为精确地界定网络主权的概念,对于上述问题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国际协作与互助 尽管在当下,数据本地化的举措能够取得相应的成效,但是从互联网和大数据经济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一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与外界的数据传输。
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向第66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旨在推动以各国政府为主体的多边主义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制定。[16]参见张硕:《主权突破领土: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国家的一种面向》,未刊稿。甚至美国的邻国加拿大,虽同属普通法系,其宪法和司法判例也不保护仇恨言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网络主权应该根据不同层次的法律框架进行分层建构,才能将抽象意义上的网络主权观念变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规制。德国甚至还提出创建申根路径的设想,使数据可以在申根国家范围内自由流动。第二,国家对于位于其领土上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保护——无论从财产法的意义上,某个基础设施属于国有还是私有。
[1] 对中国而言,捍卫网络安全、维护网络主权更是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雅虎公司辩称,依据美国宪法,拍卖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保护纳粹言论及其表达形式,因而不应受到政府和法律的限制。
权威指的是国家从事各种活动的合法权利和正当资格。内容层则随着早期互联网信息无界流通的弱化趋势,日益体现出多元化和自主化的面貌,该层面的网络主权实际上处于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和相互依赖的主权之间。
而对于需要境外传输的数据,也要求必须在俄罗斯的数据库中进行初始收集或更新。这是因为,就规制和法律建构而言,互联网各个层面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别。
第二个层次则是多利益相关方在ICANN框架之下,对ICANN的治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逻辑层和内容层中,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各国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愈发深入,使得国家的力量已经无法完全切断各国间的相互联系。[58]此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雅虎认为互联网无法提供用户地理标识,巴黎法院则认为,过滤技术已经可以探知点击网站的用户身处何方,适用何地法律。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各国行使主权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管理。
尤其在斯诺登事件后,各国纷纷意识到维护网络安全对于一国主权的重要性,网络主权(cyberspace sovereignty)也因此成为讨论主权概念的新的维度。在这些威胁面前,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完全依靠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来解决问题。
例如,2017年3月1日,外交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也强调以尊重国家网络主权为基础的网络空间治理和国际合作。[32]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塔林手册》开门见山地点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并肯定了网络主权的存在: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对于整个网络空间的主权,但除非被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如国际人权法——所禁止,一国可以对其主权领土之内的网络基础设施、从事网络活动的人员和网络行为实施控制。
[15] 然而,主权并非单一的概念。其次是逻辑层,主要包括各种传输协议和标准,如著名的TCP/IP协议。
从美国的互联网治理观念来看,私营机构之间的协同相比政府或政府间组织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和互联网发展。二是国际法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即一个政治体获得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获得国际法共同体的成员资格。2013年,美国两党更是共同签署了《2013年国家网络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NCCIP法案),以加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换言之,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该国的主权者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不受其他国家的挑战和干涉。
此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则更多体现为一国独立自主的网络生存权和发展权。[36] 具体到国家政策层面,虽然美国政府和舆论在政治修辞层面否认网络主权的概念,主张网络空间的绝对自由,但在针对物理层的网络攻击问题上,实际决策者仍然秉承传统国际法上的主权概念和主权思维——不仅一直坚持美国主权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共和党如此,而且就连一直提倡国际化和全球化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民主党也是如此。
因而,这些概念本身带有着非常强的领土性和防卫性。[60]对于部分重要敏感信息的跨境流动,澳大利亚也予以限制。
与此同时,有部分学者从网络的特性出发,认为网络主权的核心是信息主权或数据主权。而德国宪法法院则不将其纳入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